
他是一位智者,但从不展示深奥,不满口经典语录。他曾位居拉卜楞寺首席秘书之位,但从未见他言辞滔滔,扮演菁英,炫耀笔墨。他留给众人的印象是,眼神慈善,语调平稳,举止谦和而儒雅,正如他的书法,沉淀着一种古老传统的现代形态,令人心驰神往而又净土无疆,天域开阔自由。
许多藏人的书架上,几乎都藏有他的《毛兰木藏文书法乌金体》,透过一行行行云流水般的文字,那珍藏在笔锋背后的气韵和优雅,不禁令人回想起吞弥•桑布扎初创藏文时的那份豪迈之气。
有人这样形容三十个字母被初创时,他那份新生的喜悦:
三十个辅音字母押着“啊”字的韵脚率先舞蹈起来,四个元音字母稍后安静的跟进,上加和下加的符号是飞翔的羽翼和风轮,前加和后加的符号则是助行的拐杖。
字母的组合排列是需要悉心甄别的,不能乱了群舞的阵脚,词语的润色是需要悉心推敲的,否则岂能活色生香--------啊啧!
照亮雪域暗夜的明灯就要点亮了,拂去心灵尘埃的清风将要吹临了。
公元七世纪,这位藏族文明时代的首位学者,创造了一个将极易失散和流落的记忆定格于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上的文化符号。
藏族,从此被文字凝聚成一个不易解体的民族,站立于华夏民族的土地上,以她独特的个性,书写着人们内在的属性和外显的样貌。
毛兰木先生正是秉承了这样的传统,把自己一生的心血与精力倾注在藏文书法的学习与教育中,倾注在藏文典籍文献的整理工作中。

1928年,毛兰木出生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博拉乡一个名叫洛亚塘的小村里。
儿时的他天资聪颖,心灵手巧,喜欢读书写字,11岁时,他被父母送到离家乡不远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寺拉卜楞寺出家为僧。
拉卜楞寺不仅是当时名贯三藏的格鲁派重镇,更是大德辈出,学风严谨,人们心驰神往的学术圣地。
在拉卜楞寺,他先后拜大格西拉木慈成、嘉央勒协、毛尔盖•桑木旦等学者为师,系统学习了藏语文法、诗学、声明学、因明学等传统学科知识。
他聪慧好学,性格温和,得到众多高僧的佑护,特别是毛尔盖•桑木旦—— 更是一位在藏传佛教教义的阐释,藏传因明学方面造诣深厚,擅长于研究诗学理论和传统格律诗创作以及藏文书法的大师。
在他的呵护与关注下,毛兰木先生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掌握了藏文行书与楷书的写法,师生情谊也从此绵延终生。
藏文书法艺术,可以说是伴随着藏文的诞生而延伸,分为“乌金”体和“乌梅”体两大类。
据《藏文文法详解》一书介绍;
最早出现的“青蛙分腿式”的书法艺术,源于吞弥•桑布扎亲创,随后出现了新的“拼砖”体书法,许多优秀的书法大家层出不穷,先后出现了“雄鸡下垂”、“白毡展青稞”、“珍珠穿线”、“蜣螂分腿”、“鱼跃水面”、“狮子跃空”、“薄金四方”等不同的书法形式。
20世纪初,还出现了娟秀的短腿体和长腿体,自成流派,各领风骚。
拉卜楞寺奉行的书法流派是在第二世嘉木样活佛时源于藏传佛教大师蚌译师的“琼布玉尺”的书法风格,毛兰木先生在潜心学习的同时,又不拘泥于流派,悉心学习卫藏地区的“乌梅”体。
在拉卜楞寺期间,先生又拜孜仲土登丹增大师为师,在孜仲大师驻锡拉卜楞寺期间,六年潜心师旁,将“甘丹新体”、“卫藏旧体”、 “短体”、“长体”等以布达拉宫新体为主的诸多书法流派融会贯通,在众多学子中脱颖而出。
1944年,毛兰木先生17岁,参加了由嘉木样活佛亲自主持的书法大试,在六十多位竞争者中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第一名的荣誉,接受了第五世嘉木样大师的奖赏。
从此,声名鹊起,1953年,先生24岁,被第六世嘉木样亲点任命为拉卜楞寺“译仓”的大“仲义”,从此,人们尊称为仲义毛兰木。
从1939年入拉卜楞寺为僧到1953年参加革命工作,在拉卜楞寺这座藏传佛教古刹大寺中,毛兰木先生度过了15年的岁月,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伴随着20世纪中国剧烈的历史变化,经历了生命中最亮明也最艰辛的求学生活。
他的慎思、明辨与笃行,培养了他细腻、沉稳的个性,这既源于对知识的渴求也源于拉卜楞寺严谨的培养。
这种长期积淀于内心深处的感触,通过书法又外化于行云流水般的笔锋。
可以说,拉卜楞寺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启航和第一次搏击。
那些高僧大德的言传身教,成为他人生中永远珍贵的回忆。
1953年,毛兰木先生离开寺院加入了革命工作的行列,在夏河县政协任副秘书长一职,直至1958年。
在这五年期间,毛兰木先生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倾注在基层工作上,任劳任怨,勤奋不怠,始终坚守党的爱国爱教政策,在自己熟悉的民族与宗教工作中大显身手。
同时,他依旧以习字为乐,在竹笔与墨汁运走的写意中,游走于精神的高地。
那时,毛兰木先生的字已潇洒流畅,深厚有力,个性风格,倾泻笔端。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先生无法幸免,在无休无止的大批斗中,身心遭受严重的创伤。
因有过僧侣的身份,他的工作被迫终止,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一连串的批斗,致使先生听力受损,此后每每与人讲话,都是一手抚耳,提声亮桑。
这场政治灾难,使许多人蒙受冤屈,甚至被迫害致死,也有许多人从此心灰意冷,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但先生常言:
“阳光总要穿破乌云,这只是暂时的厄运,但总会过去的。
”他说:
“许多伟人也遭受这一浩劫,甚至被迫害致死,我已经是幸运的人了,偶有沮丧,但绝不失望。
”他坚信这样的状况总有一天会有改变,党和国家一定会好起来,无论如何艰难,先生从未动摇过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信念。
1978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乱反正。
先生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二次学术与书法艺术的春天。
这一年,先生来到天府之国——成都,在这里他与来自全藏区著名的学者一起,承担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组织实施的大型文化项目——《藏汉大辞典》的编篡增补与修订工作。
《藏汉大辞典》是一部以词语为主兼收百科的综合性藏汉双解辞书,是在1979年出版的《藏汉大辞典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修订的。
主编张怡荪先生从1928年开始搜集、整理国内自清代以来编印的藏汉辞书以及国外出版的藏文资料,曾在抗战末年写成蓝本共十大册。
在经过诸多藏汉学者的编写,制定增减后,虽试印出版,但是几经搁置,直到1978年立项,才重新启动。
《藏汉大辞典》的编纂,是改革开放初期民族文化恢复发展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藏学界知名人士,汇聚成都。
著名学者才旦夏茸、东噶•洛桑赤列、毛尔盖•桑木旦、钦绕威色等老一辈学者将自己的学术专长,智慧全部奉献在这部辞典中。
在成都的三年中,毛兰木先生终日与这些学者为伴,他们各自都经历了生命中最严寒的季节,在天府之都,满目碧绿、繁花似锦的时候,又共同迎接了民族文化复苏的春天,曾经被压制的“三十个字母”,曾经丧失的学者的尊严,在这个时候,都得到了恢复、保护并共同见证了文化生命中的黄金时代。
毛兰木先生在编纂工作中,主要承担佛学词汇的收集和注解工作。
这也是这部辞典所收的五万三千多词条中比重较大的部分,先生十分珍惜这份工作,查阅大量梵藏字典、学者著述及诸多注疏本,收集词条,同时广泛搜寻正字学、诗学、词藻学、医药学、天文历算、因明学等学科中与佛学关系密切的词条,扩大收词范围,并一一注解,载入书目,投入了大量的心血。
1985年《藏汉大辞典》出版,先后印制两万套即告售馨。
1987年获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学一等奖。
主编张怡荪老先生这样写到:
“初志待酬,感慨系之。
全国各地藏语文工作者萃极一堂,使我望九老苍心情十分舒畅,并可告慰一切对辞书寄予殷切期望的读者。
”这也是毛兰木先生的心声。
朝斯夕斯,无间寒暑,如秉烛光,温暖后人。
这时先生的书法,不仅笔锋优美,更显露出了一种平和与宁静的气韵。
技巧与精致已隐约而退,展露出的是生命被洗礼过后的坦然,是一种包含了生命与宗教情怀的安然与释怀。
厚积薄发,立志民族教育事业
1980年,毛兰木走上了从事民族教育工作的路,担任了甘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学校(现改名为民族综合专科学校)副校长、名誉校长一职。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藏族教育百废待兴,民族教育在迎来春天的同时,面临着更多的艰巨的恢复与探索工作。
如何在民族地区办好一所既有民族文化传统传承,又具有一定前瞻性的特色学校,是当初民族学校建设者们最关切的问题。
毛兰木先生坚持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在加强和普及母语教育的基础上,逐步摸索,培养一批既有自己民族文化特色、专业基础扎实、又能胜任未来民族教育工作者的学生。
先生充分发挥自己学有专长的一面,主动承担、积极编写教材,亲自讲授,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断增订与修改。
1987年他编写的120多万字的12部教材获全国中小学教材藏文审订委员会的好评,藏族著名学者东噶•洛桑赤列等多位学者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在民族学校工作期间,先生孜孜以求,诲人不倦,传授知识,他先后开设了《藏文正字法》、《藏文文法》、《藏文书法》等课程。
他的课堂总能用传统文化的美德灌浇许多曾经荒芜过的心田,他平静的目光,总是传达出藏族知识分子的温良与节制,他幽默而略带自嘲的话语,总能让学生开怀大笑,明晓道理。
在学校里,先生亲自给学生上藏文书法课,手把手地教他们临摹,反复练习,直至满意。
他还把自己的书法技巧毫不保留地教给那些希望得到他真传的学生。
许多人因为他的教导而受益终生。
大家都说,先生是真正的良师益友。
在这期间,毛兰木还承担了大量的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经他审订出版的著作有《安多政教史》、《柱下遗教》、《拉卜楞寺志》、《卓尼版藏文大藏经目录》、《二世嘉木样活佛传记》、《章嘉国师传》、《贡唐丹贝卓美文集》,并获得了中国北方十五省系列丛书优秀成果奖。
1987年,先生应邀前往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担任教师培训班的书法课教师,期间他编著了《藏文书法智慧珍宝》一书,融书法理论与实践为一体。
先生亲自执笔,亲自传授,许多学生至今记忆犹新,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珍藏着他的笔墨,视如珍宝。
先生得到过许多的奖项和荣誉:
1988年获得全国书法一等奖。
他先后任甘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学校高级讲师、甘肃省政协常务委员、甘肃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甘南州政协副主席、甘南州文化艺术联合会委员等职务。
直到1990年1月8日,因病去世,走过了生命中的62个春秋冬夏。
有人说少年时代是诗歌的时代,青年和中年是小说的时代,老年就变成散文的时代。
先生的少年,在故乡的自然天籁中承受父母的爱怜健康成长。
家乡的草原、蓝天与白云,应该筑就了他生命中青春的华章。
诗歌虽然没有成为他涉足的重要领域,但诗歌的气韵与节奏,则化成他笔下书法中的灵气,飘逸而又温暖地诠释了字如人生的道理。
青年时的先生,置身于古刹佛寺中,拉卜楞寺赋予了他受益终生的学养和开朗、豁达的人生态度,为他打下了人格和思想上的基础。
中年的他经历大起大落,但终于自立而成熟。
他恪守自己的作人原则,不畏艰难、不卑不亢、不哗众取宠、亦不处处抵触,他有人父的慈爱和庄重,勇于承担;
他有为师的职责,以自己的行为,诠释文化的力量。
他的笔韵经由年轻时的青涩而抵达随心所欲的自由,并沉淀成一种华贵与平静的韵致,春花看尽,无怨无悔。
对于一个藏族学者而言,他深知生命终点的指向是生命再次造访的通道,犹如他的字,修写人生,亦诗化人生。
哲学家罗素说过这样的话:
生命是一条江,发源于远处,蜿蜒于大地,上游的青年时代狭窄而湍急;
中游的中年时代宽阔而平静,下游的老年时代,汇入大海,生生不息。
大海接纳了江河,又结束了江河。
如果我们面朝大海,那海的深沉博大和奔腾的浪花就像是先生的行书,铺展于天际,留存于记忆。
来源:青海湖网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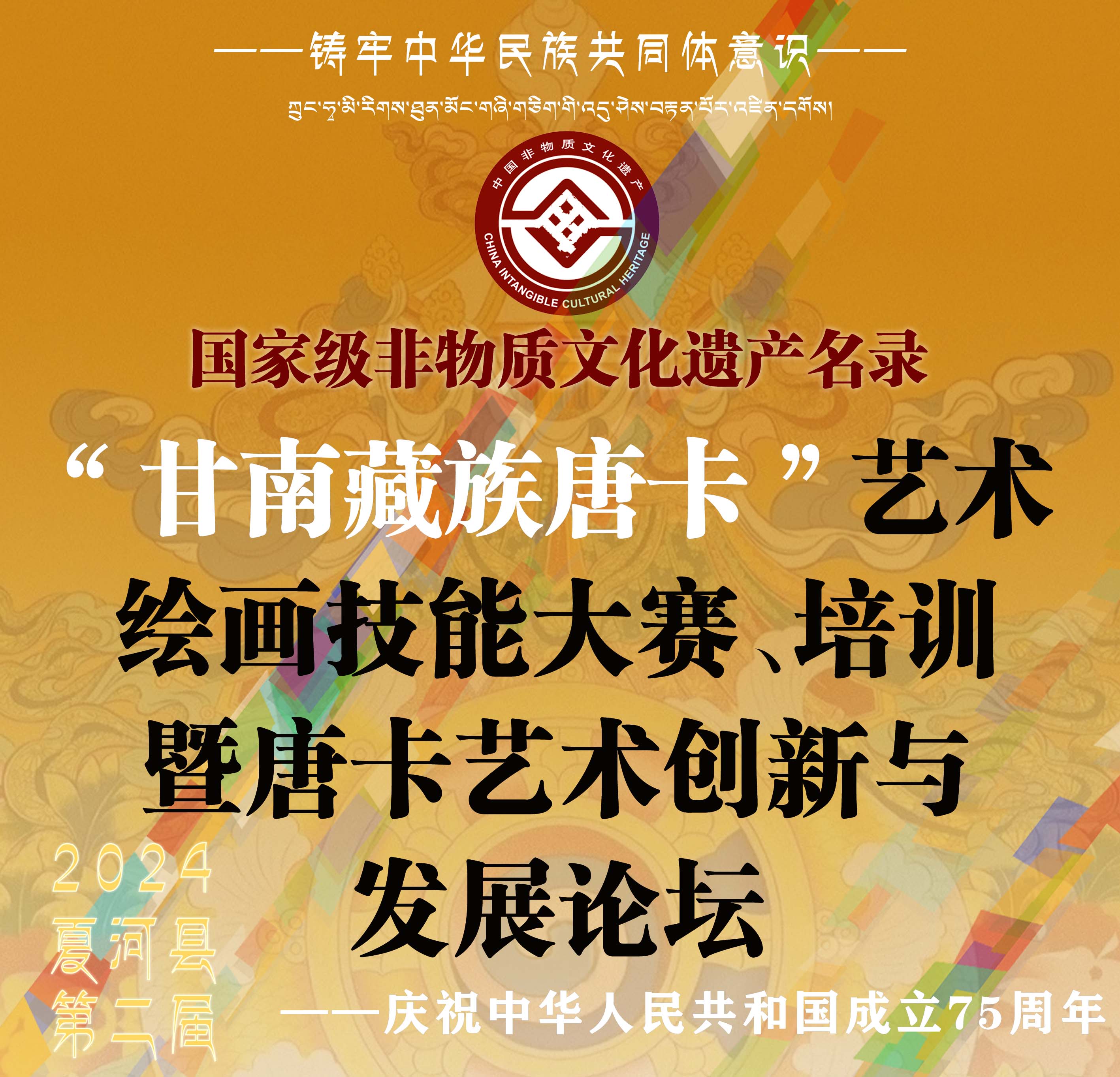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